是乔妍,还是许妍?——从小说《大乔小乔》的影视改编谈起
来源:文汇报
2025-10-22 10:26
对话人:张悦然 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黄昱宁 翻译家、作家、评论家
去年跟张悦然闲聊的时候,第一次得知她的中篇小说《大乔小乔》被同时改编成了电影《乔妍的心事》和电视剧《许我耀眼》,当时就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我熟悉这部小说,以至于当时一听片名,就依稀能窥见两个完全不同的班底阵容和改编思路——是乔妍还是许妍,她们与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2025年,《乔妍的心事》和《许我耀眼》先后上映,我都看了。具体的作品摆在眼前,人物陆续从纸面上立起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走过来,我的好奇却并没有丝毫减少——因为“乔妍”和“许妍”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许我耀眼》的热播,在网上引发了异常热烈的讨论,我看到好几个圈内人都“后知后觉”地发出惊呼——这真的是同一部小说改编的作品?同一部故事真的能有两种甚至更多种截然不同的讲法?
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现象,它涉及从文本到影像的转化时,文学到底能有多大的弹性,以及这种弹性能带来多少种可能。
这场讨论最合适的对手当然是小说作者,那个最初给了乔妍或者许妍生命的作家。于是我找到了张悦然。在这个异常忙碌的十月,我们从线下聊到了线上,从国内聊到了国外。——黄昱宁
黄昱宁(以下简称“黄”):首先还是要祝贺《大乔小乔》这个故事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改编版本都已经先后跟观众见面,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获得了认可。我的感觉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是三个有着相似的人物设定框架、但其实两两之间都截然不同的故事——但它们反过来可以证明《大乔小乔》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和成长性的故事,它适合被赋予不同的想象力,捏出不同的形状。
所以,首先我要问的是,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特别新奇有趣的事情,或者值得一说的、由“跨界”带来的冲突与启发?
张悦然(以下简称“张”):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小说与电影,小说与电视剧,这几种艺术媒介的呈现方式和受众是多么的不同。小说的成立,不等于电影的成立、剧集的成立。电影和电视剧必须在自己的形式中,探索其合理性。改编是一种重新创造,原来的小说只是一个蓝本,一张可以背叛的图纸。
此外,从小说刊载到电影或剧集问世,这当中有一定的时间差距,电影和剧集一方面在演绎小说里的故事,一方面也在与当下的大众情绪、话语表达方式共振,它们需要实现的同步性,远远高于小说。这些也是在改编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黄:在小说里,乔妍姓许——因为在15岁那年,办身份证的时候,她改成了姥姥的姓。许妍和她的姐姐乔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困在原生家庭困境里。她们的父母,将平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将无法化解的一腔怨恨,分摊在了姐妹俩羸弱的身躯中。
到了电影里,乔妍一直是乔妍,没有姓过许。整部电影在情节走向和人物轨迹上,都与小说相去甚远。也许,考虑到对历史伤痛的深度剖析是文字而非影像的专长,所以这一部分在电影里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和淡化。姐妹俩复杂暧昧的关系被简化掉了光谱中的灰色地带,剩下了大体上非黑即白的两极。“身份”的合法性成了电影情节线上的矛盾焦点。为此,编导特意把故事发生的场域搬到近年影视剧最喜欢征用的颇具隐喻色彩的云南和缅甸。跨过那道神秘的边境,跟着于亮私奔的乔妍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把“乔妍”的身份留给妹妹。当这个具有唯一性的“身份”在多年以后成为可以要挟大明星乔妍的软肋时,这个故事就被激发出一系列更容易纳入商业逻辑的连锁反应:绑架与逃离,控制与反控制,戏中戏(在戏里演孕妇的乔妍与戏外当真孕妇的姐姐,与当年死于生育的母亲的命运遥相呼应),明星的自由意志与资本裹挟……你怎么看待电影处理姐妹纠葛的方式,对云南/缅甸的地理设定又是怎么看的?
张:小说《大乔小乔》里,两姐妹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的父母。父母变成了未被妥善处理的“历史”,影响着两姐妹的人生。姐妹两人的分歧,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姐姐选择承担,妹妹选择摆脱,矛盾由此产生。但是在电影里,可能需要更直接的方式,来展现姐妹之间的冲突。于是代表着历史的父母,被换成一张身份证。两人只有一张身份证,谁都想要,矛盾变得一目了然。“身份证”也很好地将小说里妹妹希望取代姐姐、成为姐姐的心理活动外化了。
《乔妍的心事》的导演加入之后,将自己的身份背景带入了这个故事。小乔生于云南,长于缅甸,那片炎热、繁茂的甘蔗林,成为她甩不掉的过去。它与现在时里寒冷阔大的北京,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极致的差异,在小说里并不是很必要,甚至显得过于刻意,但是在电影里,过去和现在的截然不同,建构出了人物心灵世界的纵深,我认为还是很必要的。
黄:电视剧不像电影那样左右为难,它并没有试图在努力遵循商业片逻辑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堆叠上文艺审美——它显然完全在按照前者的规则运行。一开头三集讲的都是主持人许妍(这个姓氏显然捡回了小说的情节)如何雇佣演员假扮父母,打入富豪沈皓明家,互相真真假假地“猎取”,一步步靠近嫁入豪门的梦想——但这个梦想里当然预埋了后来随时可能爆的雷。直到第四集,姐姐乔琳才来到北京,姐妹之间的关系、原生家庭的阴影,这些设定都还有迹可循,但重心完全落在许妍这个人物上——“‘许’我耀眼”这个标题也说明了这一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尽管电视剧节奏飞快,特别通俗,但在塑造许妍这个人物的时候,紧紧抓住了原著里的一句话:“(许妍)想从人堆里跳起来,够到更高处的东西”,并用很多简单有效的情节剧的方式,将这一点强化、放大。你怎么看待电视剧的改编?
张:电视剧的确完全围绕妹妹许妍展开,展现了她是如何在大城市里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童年爱的缺失变成她迫切想要出人头地的缘由和动力,由此生出嫁入豪门的愿望,似乎变得很合理。我记得在小说刚发表的时候(2017年),有人跟我探讨它的影视改编时提到,可能需要改掉许妍希望“嫁入豪门”的设定,因为观众可能无法认同这样“虚荣”的人物。但是几年间,观众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彼时的“虚荣”变成了现在的“真实”。“欲望写在脸上”成了一种褒奖。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许妍的职业变化。2017年的时候,还有更多传统的电视节目及主持人,随后几年里,电视节目少了,这种主持人也少了,如果许妍一直做美食节目主持人,似乎很难展现出人物的活力。电视剧的改编中,编剧很巧妙地将“直播”“创业”这些当下热门的职业,加入到许妍的人生履历里,让这个人物变得更有生气,更真实可亲。
黄:我这两天也在重读《大乔小乔》。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影视行业会不约而同地看中这个故事,觉得它适合被改编。它确实自带一些时下的热点问题,这些话题在小说里表达得很简洁,但保留着复杂和暧昧的光谱,折叠着多层次的延展空间。到了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是怎样被大刀阔斧地简化,如何被突出和放大其中的“爽点”,如何不深究现实逻辑,毫无压力地放大反转的“钩子”——这显然是一种短剧化的叙事方式。
我的疑问是,当这样的影像改编方式大获成功之后,你对于小说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新的看法呢?是觉得这两种艺术形式本质上如此不同,所以更相信文学无法被替代呢,还是会因为新一代受众口味的变化而对传统形式的小说的前途感到忧虑?你究竟是信心多一点,还是担心多一点?
张:我觉得严肃文学和当下的电视剧确实相距很远。想要成功转化,改编的幅度可能就会很大。小说最终提供的可能是几组人物关系,或者是主要人物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释放出很大的力量,但前提是创作者必须相信这一点。
现在电视剧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效率在不断提高。观众习惯了这种效率,也将这种标准用来评鉴严肃文学,如果是这样,他们势必是会失望的,因为严肃小说里容纳的故事没有那么多,也很难有那么多大开大合的转折。而且留白太多,让读者自己要做的“作业”太多,这些都是严肃小说对读者形成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严肃文学读者的减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我对小说的未来还是有一些信心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觉得人们很快会对那些范式化的、重复而缺乏创意的叙事感到厌倦。真正有创造性的叙事,则会凸显出它的意义。
黄:“让读者自己要做的作业太多”——这个确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读者到底还能不能从“做作业”里获得乐趣。
小说里其实特别动人的部分是许妍和乔琳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以及结局时许妍替乔琳抚养孩子的那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接力”的关系——仿佛一个人的生命借助另一个人继续活下去。原著里有这样一段话:“许妍说,你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当初就不会那么希望了。乔琳说,我还是会那么希望的。我从来都没觉得不该有你,真的,一刹那都没有,我只是经常在心里想,要是我们能合成一个人就好了。她握住了许妍的手。她的手心很烫,仿佛有股热量流出来。”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这层意思,通过镜头语言;电视剧则完全抹去了原先的悲剧色彩,变成浅显直白的喜剧,让她们很快在逆境中结盟,共同创业,在网上做起了服装生意。
但说实话,我还是更怀念小说里的写法,它让我想起很多我们熟悉的小说。从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到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理想女性的完整人格似乎都是需要互为镜像的一对拼合而成的——都在或多或少地表达“要是我们能合成一体就好了”。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问问你是怎么理解女性文学中这个“互相完善”的母题的?在你的小说中,是不是也包含了这样一份“作业”,需要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一起来解答?
张: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能写哪些主题,会写哪些主题,几乎是很命定的事。两个女性之间的镜像关系,好像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我的主题。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樱桃之远》里,就有两个命运紧密相连的女孩。从那之后,两个互为镜子的女人,就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大乔小乔》里是姐妹,到了《天鹅旅馆》里是主仆。很多时候这并非我刻意所为,只是当我把其中一个写出来的时候,另一个就会跑进故事里来找先前那一个,就好像她们是成双成对的,只写一个人的故事是不可能的。或许我觉得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飘摇的,无所依傍的,真正可以与她产生连接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女人。是那个女人让她能够看到自己,帮助她成长。我发现在文学作品中,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在面对另一个自己(the double)的时候,态度很不一样。男性人物通常想干掉那个像自己的人,这很好理解,因为那个人的存在,威胁到了自己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意义。但是女性人物,面对“另一个自己”,则是想和她“合为一人”,这个想法含有一种悲伤的色彩,似乎暗示了女性天生觉得自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最终,不管现实如何,女性人物总是会将“另一个自己”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她的精神世界因此变得更开阔。《大乔小乔》的最后,大乔死去了,但她也内化为小乔的一部分,真的与小乔合为了一人。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点击右上角 QQ
QQ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QQ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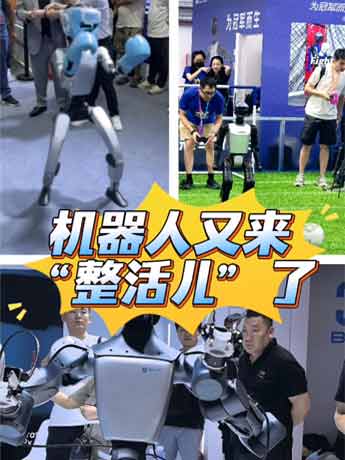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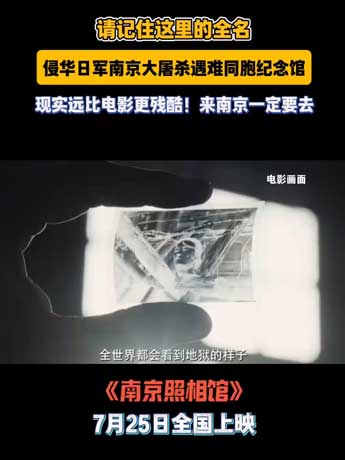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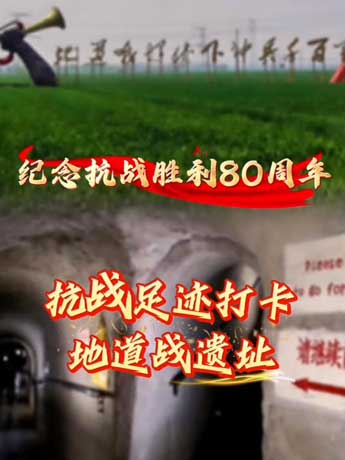











“可降解”不是污染环境的理由